当我开始把大脑里那一片惺忪和朦胧慢慢打开、能够形成一点感知和记忆的时候,有四个红色的大字随着我的整个世界一起逐渐清晰;朝阳饭店。
如果还要配上什么背景,就是刚刚清扫过的南大街头那些随晨风飘落的洁白槐花,还有我手里提着的那个钢精锅。
我肯定已经无法想起自己第一次去朝阳饭店“舀汤”是什么时候,四岁还是五岁?
看着已经三岁多的涂涂,我不太敢相信自己那么小就单独去买牛肉汤,去和那么多的大人一起排队,去把钢精锅放在比自己还高的、盛牛肉汤的台子上;可是我确实在一岁多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自己扶着墙从三复街走到南大街的舅爷家、因而让全家人急得直哭的惊人事迹,而且想一想那时候和我一个岁数自己去买汤的孩子不在少数,于是我还是觉得四五岁时自己去买牛肉汤也很正常。

我记忆初开的时候,就住在三复街的奶奶家,也经常住在东大街的婆婆家。
如果住在东大街,我觉得除了每天都上鼓楼耍一圈永远不变之外,每天的早饭永远都不一样,蒸馍、菜馍、烙馍、菜蟒,然后是面汤、米汤、红薯汤等等等等,因为我婆婆手下不仅有我还没参加工作的二姨和三姨当帮手,而且还有我那喜欢出去买着吃的二舅和大舅带回来烧饼、油旋和油条之类。
在奶奶家就不一样了,我根本没有见过早年去世的爷爷,爸爸妈妈都是一起床就要赶着上班(爸爸还要走到西关然后坐车到涧西),所以往往不吃早饭或者去厂里的食堂解决,就剩一个叔叔上班不需要早起吧,可是他一般都要睡到很晚才会打着呵欠出来洗脸刷牙。而姑姑,那时候已经结婚住在西工了。于是只剩下我和奶奶俩人都可以忽略不计的饭量,也就没多大开伙的意思了。
于是,在奶奶家就每天早晨几乎都是舀汤回来喝,几乎每天都是牛肉汤,几乎每天都是朝阳饭店的牛肉汤。
听起来,经常能喝牛肉汤好像很奢侈,其实不然;在那个时候,自己拎一口锅去买汤的话,师傅自然会多舀几勺(你还可以要求再添几勺),往往都够一家人泡上馍解决早餐。可不管舀了多少,毕竟都只有那一碗汤的价值,有点隐约的香味和点缀的葱花也就算了,肉是偶尔才会遇到那么几片。
别看“一碗”牛肉汤被一家人分着喝,可是奶奶也是在三个儿女都参加工作以后才舍得经常喝牛肉汤的。家里一般都是一个人去舀汤回来,然后我和奶奶泡上蒸馍喝汤,爸爸妈妈偶尔也喝,喝完了剩下的汤,还够叔叔起床后吃一顿(如果他不出去喝汤的话)。
最早,去舀汤的都是奶奶,后来我长“大”了,就是我去。
经常都是迷迷糊糊地去,最多走的时候被交代一句“召着钱掉!”或者“记着放辣椒时候把锅盖翻过来!”听着这些叮嘱的时候,我已经在很深的院子里走过了不少曲里拐弯和上下台阶;
走在三复街上,遇到的多是匆匆上班的人,还有已经舀汤回来的人们,看着他们手上的锅沉甸甸地摇晃,我偶尔会眼馋他们他们反扣的锅盖上那些摞着的烧饼或者油旋;和他们其实一样,我们有时也吃,但还是吃自己家的蒸馍居多。
不知不觉地,就会转到了南大街;在身后农校街口那家豆腐汤的嘈杂声中,面向北边继续迷糊着走去。
当太阳“正式”地升起之后,南大街就会成为服装的海洋,尤其是满街的裤子,伴随着的是有点挤不过去的人流。可在我去舀汤的清晨,这里是一片难得的寂静;这是个很奇妙的现象,人们往往会对公园或者野外的寂静留下一个不过尔尔的印象,但是会对往往的闹市地界里难得的寂静时光记忆尤深。
冬天的南大街,早晨只是干燥的气息和剌手的寒冷,我能听到钢精锅随着自己的偶尔发抖发出一点响动,远处扫街的师傅们“簌簌”的扫地声,让我感到地面坚硬的寒冷。
春夏时分的南大街则要靓丽了许多,特别是槐花盛开的季节,让我这个根本不知道何为美丑的孩子单是看着她们飘落的身姿就有些入迷,有些傻乎乎地边走边看,或者还会用脚去趟那些地上的槐花,满街有些白花花的街道,似乎让自己在一片温暖的体温里偶尔回到原本只有寒冷才能换来的雪景。
秋天,这段路则会有些让人讨厌,枯叶不停地落在脸上,甚至是回去时的辣椒里,看着那些扫完的街道须臾之间在一阵风中再次落着树叶,我会看看那些已经习惯这一切的清洁工师傅们;他们能扫干净吗?

很快地,就到了朝阳饭店;这个让我有点想顶礼膜拜的地方,总是在我到来之前就站着一队买汤的人,还经常一直排到门外。
我站在他们面前,那么小,他们好像也看着我,按照我四五岁的经验,他们一定是在说;“这孩子头咋这么大?!眼咋这么小?!”
买了张票,然后打着瞌睡站在排得很有秩序的队伍里,我闭着眼睛听着周围的声音;这里每天都响彻不停的,除了那些“不要葱”、“多撇点油”(那时候几乎没人要清汤)、“双椒”之外,就是此起彼伏的熟人打招呼的声音。除了伙计、同事、邻居,还经常会有亲戚;“二达”(二叔)、“姨夫”、“姑奶”、“四妠”之类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就在这些所有的声音中,打着盹,慢慢琢磨着各种称呼所代表的亲戚关系,还有盛汤的套路和速度;然后随着身边的氛籁,不时本能地挪动着脚步。
轮到了我,把锅盖翻过来,放上票,然后踮着脚把锅放到盛汤窗口的台子上,探着头交代一句“辣椒搁到锅盖上。”
然后就是里面的一顿折腾;最初的时候我还会探着头看看,后来已经没有任何好奇的感觉;基本上听到师傅放铁勺子的声音之后,就准备接钢精锅了。
师傅把身子探出很深,一边双手掂着锅慢慢放下,一边对我说一句;“小开(方言,即“小客”之意),接好!”
然后的事情,就是我在排队的、添汤的、喝完走人的人流中,拎着锅,小心翼翼地看看锅盖上那摊红汪汪的辣椒油,走出朝阳饭店。

等我回到家,奶奶已经准备好了碗。她把我掂回来的汤按碗盛好,摆上馍,然后和我开始早餐的整个过程;
中间也许会有爸爸妈妈进来、吃完,走人,反正我和奶奶就那么慢慢悠悠地喝着;她她是掰一口馍放进嘴里,然后喝一口汤,我是把一大块儿馍放进汤里,然后偶尔换个角度咬一口馍,没完没了地喝着玩着;
现在想起奶奶的样子,觉得她好像就是那样独自带着孩子们过了很多年;坐在暗暗的屋子里,看着窗外,慢慢地等待着什么,等着时间过去,等着我慢慢长大,不再边吃边玩;
吃完了朝阳饭店的牛肉汤,我和奶奶坐在门外的屋檐下,玩着扑克或者跳棋,或者看看屋檐上滴下来的水帘子,或者看看冬天里房檐上挂着的冰柱子;
在似乎已经停止的光阴里,忽然会有刚起床的叔叔从屋里探出半个身子,对奶奶说;
“妈,给汤热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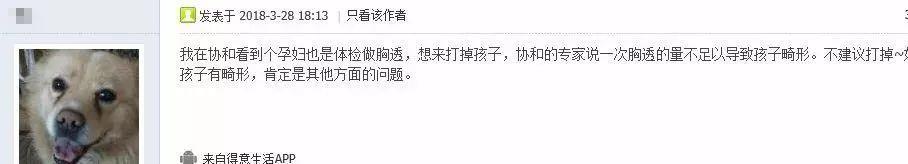





-3P.jpeg)